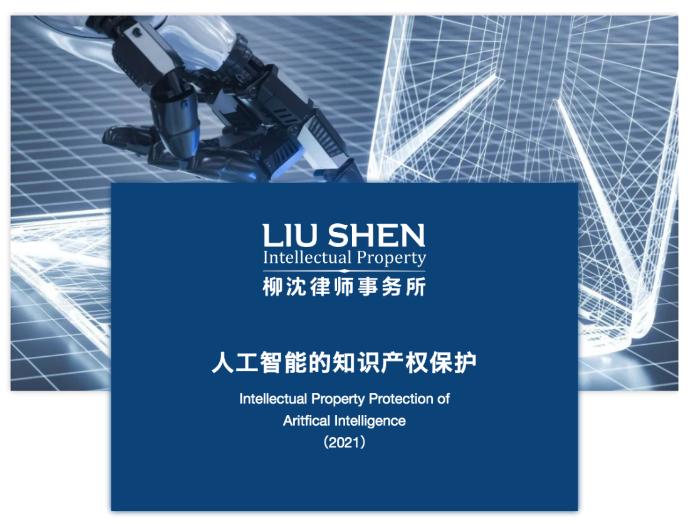
点击章节题目阅读其他章节:
第二章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知识产权的立体保护和专利申请态势

第六章 人工智能的商标保护
人工智能(AI)目前在中国属于热门的领域,无论是国内阿里、腾讯、百度这样的大厂,还是国外IBM、MICROSOFT这样的巨头,抑或是为资本所追捧的初创科技企业,大都涉及AI领域,后者中的一部分发展成为了新兴的独角兽企业。
目前,大多数有关AI在知识产权领域保护的文章都着重于专利、版权和商业秘密,而对于AI在商标方面的保护和影响涉及极少。本章试对AI的商标前期布局和后期保护进行分析,希望对企业有所帮助。
6.1 AI的商标前期布局
无论是在主要依靠“在先申请”决定商标权归属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和法域,还是在主要依靠“在先使用”决定商标权归属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都需要尽早在当地或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体系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争取一个较早的申请日。
提交AI商标注册申请前,有两个方面的事项需要确定,一是选择合适的AI商标,二是指定相应的商品和服务。
选择合适的AI商标的问题在于,一方面申请人们都希望选择简洁的、朗朗上口的、含义美好甚至隐喻高科技的商标,另一方面考虑到各国各地区商标的既有存量以及每年的巨大增量,选择一个没有在先冲突商标的合适的AI商标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在大多数申请人希望全球所有市场选择相同的AI商标的情况下。
我们注意到,国内的大厂和国外的巨头在此种情况下,很多会选择用已有的主商标加上简洁上口的新名称/名词的方法,去申请注册保护新的AI商标,比如说IBM的IBM Watson、MICROSOFT的MICROSOFT AI SOLUTION、华为的HUAWEI ATLA、阿里巴巴的Alibaba Cloud、腾讯的Tencent Cloud等。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前面的已经注册多年的主商标可以很大程度保证新的组合商标顺利地通过审查,不至于和在先的他方商标轻易撞车,另一方消费者既知道使用该组合商标的商品服务是来自于哪个厂商进而产生了信任,又因为主商标后面所带的新名称/名词知道这是一个新的系列,甚至象“Cloud”和“AI SOLUTION”这样的新增加的名词还表明了商品服务的具体内容。
当然,出于种种考量,也有些大厂巨头选择采用和之前的主商标完全不相关的全新AI商标,比如百度的Apollo。这样的选择一是给消费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呼叫更加简洁;二是在其自身使用时也多了很多灵活度,注册下来后视场合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和主商标组合使用。但是这样的风险是其在先撞车商标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即便是IP策略相当完备的大公司很多时候也难幸免。比如华为在试图申请注册其AI商标“HiAI”时才发现其合作方已经在几十天前提交了相同的注册申请,后续双方就此商标进行了数年的争夺;再比如AMAZON试图在中国申请注册其AI商标“ECHO”时,也遇到了在先障碍,一时不能得到注册。因此如若选择专业的全新AI商标,公司一是要做好保密工作和合作方签妥保密协议,二是要事前做大量的检索工作评估注册的可能性,三是要及早申请抢占一个优先的申请日。但即便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有时这样的全新AI商标的注册结果也不能尽如人意,尤其是想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注册使用的情况下。
新兴的AI科技公司没有这样已有较长历史的主商标可以依仗,往往还处于选择自己的主商标用于AI商品和服务的阶段。选择一个全新的主商标时为避免太多的在先冲突商标,应尽量选择自创词汇而非字典词汇。如果自创词汇能够有对应其公司名称的元素,并能暗示科技公司属性,那么该商标在注册通过率上、市场推广便利度上和潜在的消费者接受度上,都会有较好的表现。科大讯飞的英文商标iFLYTEK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范例,其中“i”在IPHONE、IPAD、IWATCH等商标的带领下,消费者很容易将其也理解为一个代表高科技新技术的元素,且“TEK”和“TECH”谐音,也暗示了科技的元素,中间所插的一个字典词汇“FLY”一方面对应了公司名称中“飞”的含义,另一方面由于加上了前后的“i”和“TEK”元素,不至于和其他含有单独“FLY”单词的商标造成冲突。
除了AI商标需要精心选择,AI商标指定的商品服务也需要仔细考量。不同于其他的知识产权,商标的注册保护必须和相应的商品服务相结合。在AI商标申请注册前,必须要选定指定的商品和服务。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法域采用《尼斯分类》,其将常见的商品和服务分为45个大的类别。AI技术的本质是可以实现各种功能的软件程序,因此其核心保护的类别为《尼斯分类》的第9类;同时,该软件程序的升级维护等服务为《尼斯分类》的第42类。
但是,AI技术与其他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其产品和服务本身,还会被广泛地应用到其他领域。从车辆驾驶到照明烹饪,从生活家居到玩具教育,都可以看到AI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虽然很多时候,AI技术的所有者只是将AI技术提供给另一生产商,让其在其生产的车辆、灯具、厨具、家居用品、玩具和在线教育服务中使用,而AI技术的所有者本身并不生产销售这样的产品、提供这样的服务;但若AI技术所有者不在《尼斯分类》相应的第12类(车辆)、第11类(灯具和厨具)、第21类(家居用品)、第28类(玩具)、第41类(教育服务)申请注册保护自己的商标,而导致他方在这些商品服务上注册了AI商标高度近似甚至完全相同的商标,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些商品和服务中使用了AI技术所有者的技术,进而造成混淆误认,甚至对AI技术所有者的商誉造成不好的影响。那么是否AI商标在申请注册选择商品服务时就要覆盖所有这些可能的应用领域的商品和服务呢?也不尽然。
如之前提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和法域主要是依靠“在先申请”决定商标权归属,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是主要依靠“在先使用”决定商标权归属。在前者的体系下,商标申请人不需要主动提供商标使用证据即可注册维持商标;而在后者的体系下,商标申请人需要主动提供商标使用证据方可注册维持商标。考虑的商标体系的不同,为避免他方在车辆、灯具、厨具、家居用品、玩具和在线教育服务注册了相同类似的商标,而导致消费者认为这样的商品服务带有AI技术所有者的AI技术,AI技术所有者可以考虑在前者的国家和法域除了核心类别以外在指定商品服务时囊括上述所有的相关类别;而在后者的体系下,尤其是美国,对商标使用的虚假陈述和证据会导致商标失效、罚金、入狱等严厉处罚的情况下,建议AI技术所有者只对其真正使用的核心类别进行申请注册。
对比上述阿里、腾讯、百度、IBM、MICROSOFT、科大讯飞等公司在两个体系下的AI商标的申请注册,我们也确实发现其往往在前者的体系下,如中国,尽可能多的囊括了所有相关的《尼斯分类》的类别;而在后者体系下,如美国,则往往只指定了《尼斯分类》中的实际使用的类别,少于在中国指定的类别。
因此,AI商标指定商品服务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的商标实践,切忌所有国家法域一刀切一锅端,导致在前者的体系下未能得到充足的保护,或是在后者的体系下指定了未真实使用的商品服务导致后续轻则商标无法注册维护保持有效,重则遭到罚金等处罚。
6.2 AI商标的后期保护
商标申请注册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品牌,一方面需要让消费者看到该AI商标即其商品和服务来自于哪个厂商,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挡他方在相同类似商品上注册使用相同近似商标;AI商标申请注册的目的也不外于此。
商标商品相同的情况可以很好判断,但在商标商品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商品是否类似,各国各法域的实践又不相同。这样的情况让人难免产生不亚于商标混淆(confusion)的困惑(confusion)。大致说来,中国的实践往往更严格遵从《商品服务类似区分表》进行判断,而美国会更多的考量实际商业中的影响因素。而且即便是在同一国家法域,在行政确权阶段和民事侵权案件中,判断的标准和考量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比如,美国在前期的商标行政确权中,用Polaroid Corp. vs. Polaroid Elecs, Corp.一案中确定的The Polaroid Factors判断双方商标是否构成类似商品服务上的近似商标,The Polaroid Factors包括:
1.在先商标的强度;
2.两个商标的近似度;
3.商品或服务的类似度;
4.在先商标所有者进入在后商标所有者领域的可能性;
5.在后商标所有者采用在后商标的目的;
6.实际混淆的证据;
7.相关消费者的经验度;
8.在后商标所有者所提供商品服务的质量;以及
9.商品服务的相关程度。
而在后期民事侵权的判断中,美国法院遵从的是John H. Harland Co. vs. Clarke Checks, Inc.一案,其中确定是否构成商标侵权,需要考虑以下七个要素,即:
1.商标的类型;
2.设计的近似度;
3.商品的类似度;
4.零售店和消费者的身份;
5.使用广告媒体的相似度;
6. 被告的目的;以及
7.实际的混淆。
对比可见,两个判断标准多有重合,但前者更多地考虑了商标的强度和公共利益,而后者更多偏向商品实际销售的场景。
但是,令人欣喜的是,目前的中国司法实践中,考虑到AI的具体应用场景,也开始更多的考量实际商业使用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而非严苛地遵循《商品服务类似区分表》去判断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问题,进而得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结论。在百度在线公司vs.北京子乐科技有限公司(2021)一案中,被告在生产销售的杜丫丫学习机中突出使用“小杜”指代其产品;而目前市场上使用了AI技术的智能音箱、学习机等产品,消费者更多地是用语音呼叫指代产品,而非传统地更多依赖文字识别商品,这就导致原本根据文字一般不会构成近似商标的“小度”和“小杜”在此种AI技术的应用场景下极易造成混淆和误认。考虑到原告“小度”和“xiaodu xiaodu”的知名度以及被告公司主观的恶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突破了《商品服务类似区分表》,判定原告的小度智能音箱和被告的杜丫丫学习机从功能、受众、销售渠道等方面来看属于类似商品。
除了语音呼叫互动以外,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物过程中使用关键词寻找合适的商品服务时,在搜索引擎中搜索相应产品服务的信息时,AI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其中。在电商平台销售额开始赶超线下门店,搜索引擎比传统媒体更多地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服务信息的情况下,AI技术在消费者的购买决定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在此种情况下,AI技术的提供者是否会成为潜在的商标侵权者,是每一个AI技术提供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Coty Germany GmbH vs. Amazon Services Europe Sàrl, Amazon Europe Core Sàrl, Amazon FC Graben GmbH, Amazon EU Sàrl (2020)一案中,因Amazon的AI技术没有自动选择关键词,也没有主动参与关键词广告系统,因此被判定无需承担商标侵权的责任。因此,如若AI技术没有自动地有选择性地“帮助”消费者选择关键词,也没有主动参与到涉案销售商的关键词广告系统中,且AI技术提供者之后也有相应的下架程序并及时跟进落实,则AI技术提供者不应承担商标侵权的责任。
但如若AI技术的提供者在侵权行为中牵涉更多,则可能会构成商标侵权。在Cosmetic Warriors Ltd an Lush Ltd vs. Amazon.co.uk Ltd and Amazon EU Sarl (2014) 一案中,由于Amazon的AI技术在消费者使用商标搜索后触发的网站链接并不包含该商标对应的品牌产品,从而导致消费者可能对于该网站销售的商品是否来自检索商标的品牌商而产生混淆乃至误认,被告Amazon被判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AI技术提供者在前期的商标布局中,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商标,考虑不同国家法域的不同商标实践指定不同的商品服务;在后期的商标保护中,一方面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需综合考虑AI技术应用场景的特别之处来决定是否采取维权行动,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自身算法技术是否过多地、不恰当地牵扯进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决定中。



